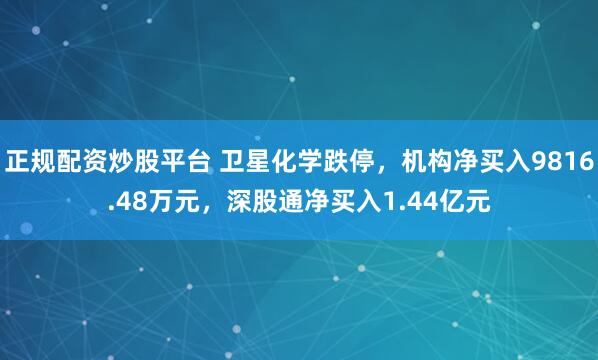“1955年11月凌晨五点,你还要把百姓全劝下山?”北高峰山脚合规配资平台,王芳压低声音问随行参谋。风里带着竹叶的清香,山路却静得出奇,连挑担的茶农都不见一个。

毛泽东第三次攀登北高峰,安全方案依旧是“封山清场”。这是王芳亲自画出的警戒线:山门封闭、村户转移、游客暂缓进山。对一个省公安厅长来说,再保险不过;可对毛泽东而言,空山无语反倒显得冷清。
登到飞凤亭,天色已亮,一只大公鸡突然从院墙里蹿出,扑棱棱落在小道中央。毛泽东止步,笑着招手:“老王,你管住了活人,倒没管住它。”一句话听着像玩笑,王芳心里却隐隐发紧——主席并不喜欢这座“真空”山谷。

傍晚回到汪庄,毛泽东没有多说。他独自提笔,在随身皮夹里撕下一张便笺,写下五律十二句。字迹未干,交给秘书送到王芳房里。王芳展开一看:“三上北高峰,杭州一望空……一片飘摇下,欢迎有晚鹰。”短短数行,却把白日里“空山无人”的尴尬写得透彻。王芳苦笑:“这是在批我们工作死板。”这段话后来在警卫口中流传成“晚鹰诗案”。
事实上,毛泽东与王芳的渊源远比这首诗早。1953年12月,毛泽东首次以国家主席身份抵杭。那年12月26日,他整六十岁。毛泽东向来反感庆生,省委只好以“接风”名义备了两桌家常菜。罗瑞卿打趣王芳:“山东大汉起个‘芳’名不够硬气,改个‘方’如何?”众人哄笑。毛泽东却摇头:“山东山岭连草都稀,你头上的草再拔光,绿化靠谁?还是留着吧。”一句双关,让厅长的“芳”字保留下来,也让桌上一群干部心领神会——主席看的是大局,不是一枚偏旁。

席间茅台每人一杯,菜已空盘,酒却剩半杯。毛泽东指了指杯子:“粮食做的,滴水也是工人汗,不能倒。”几轮推辞后,王芳端杯见底,再端再空,连干数杯,双脚并拢敬军礼:“任务完成!”毛泽东爽朗大笑,“痛快,这才像山东人。”自此二人交往更密,一位管安全,一位不设防,杭州城里常能看见他们并肩而行的身影。
1954年春,毛泽东从新登考察归来,半路突遭暴雨,王芳急忙搀扶主席躲进一户竹编老人家。王芳想把老人凳子让给主席,话未出口便被制止。“群众凳子能随便动吗?”毛泽东一句话让王芳面红耳赤,也让他把“群众利益”四个字刻得更深。
次年夏,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。王芳报到当晚直奔丰泽园。毛泽东兴致颇高,一聊便是深夜。临别时他说:“你爱喝酒,带几瓶老茅台走。”王芳随卫士进库房,兜里装满十瓶。回到招待所已是凌晨,却还是被同行干部抢走九瓶,他自己只偷偷留下一瓶,至晚年仍念念不忘那股醇香。

1955年“北高峰事件”后,王芳没敢再大规模清场,但警卫尺度依旧难拿。矛盾点就在这里:特务隐患未绝,主席却偏爱随性与群众打成一片。王芳左右为难,只能把警戒圈越收越细,把路径越算越准。毛泽东下江南八次,杭州总要停数日,他嘴里说“第二故乡”,却常被“安全规定”束缚。
1958年初夏,毛泽东又至杭嘉湖平原考察。江华提前布置迎送,车队刚进省委大院,就听毛泽东说:“不接不送,我当自己回家。”此后浙江形成约定俗成——主席来去无迎送。看似简单,其实是对王芳等人的再一次提醒:安全要做,形式主义不要做。

1974年毛泽东病中谈及旧事,对卫士李银桥说:“王厅长是好人,就是酒别再多喝。”那会儿王芳已调离浙江,却始终把杭州岁月视作人生高光:既学会了怎样守护领袖,也领悟了何为依靠群众。
返回1955年那张小小便笺。王芳事后专程跑到北高峰周边几个村子,挨户听意见。半个月后,他推开一扇重新刷漆的木门,对当地老乡说:“以后主席再来,不必离家。”安全与民意的平衡,就在这扇门里找到了新的落点。

至于那首《五律·看山》,王芳后来一直带在身边,字迹早已被折痕磨淡,却仍认得最后两句——“一片飘飖下,欢迎有晚鹰”。他私下解释:“晚鹰就是普通百姓,主席盼的是鹰群,而不是孤零零的警卫。”这番体悟,成了他往后几十年公安生涯的座右铭。
出彩速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